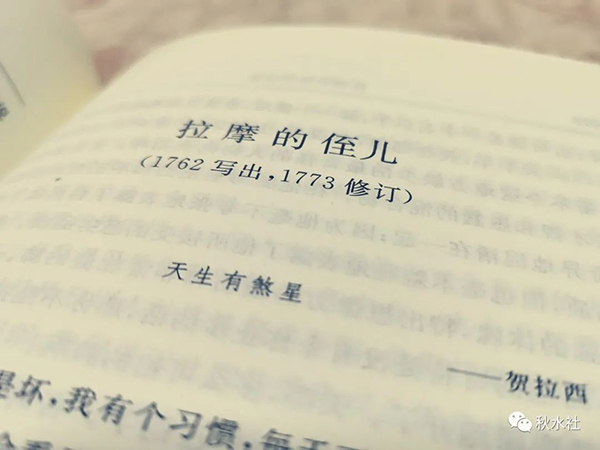
“造反派”、“保守派”与“逍遥派”
1966年6月1日,毛泽东批准向全国广播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将“文革”引向了群众运动。群众运动中出现了“造反派”、“革命派”(援引毛泽东延安时期提出的“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口号。亦称“革命造反派”)和“保守派”(亦称“保皇派”)的分野。1967年上海“一月革命”后,“造反派”一路猛进,甚嚣尘上;“保守派”则或偃旗息鼓,或匿影藏形。而后,随着谭震林等“大闹怀仁堂”的所谓“二月逆流”(亦称“二月抗争”),以及军队介入地方文革的复杂变局,文革群众运动便呈现出“造反派”多因“主义-路线”(虚)和“权力-权利”(实)之争而分裂;“保守派”则部分消散,部分改换旗号、蜕变崛起的两重态势。至此,全国各地展开了两派、三派乃至多派之间的“全面内战”。
1967年5月,高层决策掀起针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其实内含着整饬“全面内战”的需求。然而,“大批判”是喧腾的“宣传战”,为“权利-权力”的“派别武斗”才是严酷“血肉战”。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除了各派别的领军人物和骨干分子鏖战于前线外,大批的群众脱离了文革运动的现场,衍变成了“逍遥派”。
为什么逍遥派成为群体现象
到1967年,“逍遥派”已是普遍的社会存在。这个群体的经典特征被舆论概括为:你搞“路线斗争”(即“打内战”),我搞“线路斗争”(指男生装收音机、电视机;女生织毛线等),具体还表现为下棋打牌、谈情说爱、私钻业务等等。总之,不管左右争锋,背离文革运动的政治方向,自顾自地朝着娱乐悠闲、修身养性的路径上走。
于是,就有来自正规报刊的《不做小资产阶级“逍遥派”》(文汇报)和刊印于所属各造反组织的群众报刊、传单上的文章,如《“逍遥派”往何处去》(华东师大)、《坚决煞住这股“逍遥”歪风》(上海铁道学院)、《讨伐“逍遥派”》(同济大学)等,俨然站在“革命”的制高点上(此为革命造反的“常态”),指责“逍遥派”是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时期”,是在“两条路线的决战时期”,“不关心无产阶级政治”,且“逃避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而“逍遥”之实质则是“对革命的背叛”等。
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当口,出现“逍遥派”,且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群体的现象呢?造反派的文章指出:一种情况是某些人在运动中“犯了一些错误,喝了几口水”,便踯躅于岸上,一蹶不振;一种情况是某些人怀揣着个人目的参加运动,当发觉“愿望无法实现”时,便止步图安逸。如果说前者是运动中的“失落者”,即从行进着的队伍中退出,属被动型的;那么后者就是运动中的“失意者”,即从变化着的局势中退出,属主动型的。
其实,这两种情况均是正得势的造反派眼中——可称“革命近视眼”中的景象——只见曾经的“对手”退隐,却不见更广大的群众(从统计的角度说,应占各大中学校五分之四左右的学籍人口),只在文革造反8、9月间“破四旧”、“大串联”等初始阶段,随波逐流地在社会上跟随了一段(约有十分之一左右的所谓“黑五类”子女,早在“血统论”的喧嚣中就闭门了),10月份一回校园号召批判“资反路线”时,就纷纷择路而走,正面观望者有之,侧面留意者有之,绝大多数则背身而去。主导的原因不是消极生厌,逃避革命,而是这“革命的主题”已浓缩成派别的阵营和对峙,而与自身的境况、心念和需求无关,以至在校园里留下数路激进的骨干(称“头头”和“干将”),或为“主义-路线”,或为“权力-权利”而战斗就不足为怪了。
一场非常形态的大运动,只可能在短暂的“时-空间”(形势、情势之适宜),召唤起成千上万的群众呼啸着、呐喊着往前走(可称“广场效应”),其内里是有一批“非常人”在策动着和支撑着,一旦这行进的队伍走向了这“时-空间”之边缘(形势、情势之变化),必然发生“鸟兽散”般的结果。在上海,因没有发生全市性两大派之间的军械性“武斗”(上柴“联司”及“支联站”初成气候时,即被“工总司”一举铲除),各学校、各单位的造反组织多是围绕着自身利益的“内战”,由此产生大批的“逍遥派”,无疑是很正常的社会嬗变了。
三点结论
此结论有三个要点:
之一,引用惯常的说法,文革是一场“全民运动”,甚至造成“夫妻离婚”“父子反目”。事实上,即便在派性纷争最激烈的1967至1968年间,奋力投入“内战”的骨干仍是少数(头头、追随者和关系者),游离于“内战”之外的是多数,这就自然地形成了一个与文革运动的“政治场”相区隔的“社会场”。承认这个“社会场”,是研究“逍遥派”的前提。
之二,其实,“逍遥派”既没有主导的政治理念,更没有严密的组织构架,所以,它寄寓于存在的“社会场”,不是一种被指定的“时-空间”,而是自发形成的以满足兴趣、爱好、特长乃至个人情感的人际交流圈,大致有娱乐型、消遣型、安逸型、养生型、情爱型、自我奋斗型,等等。从非常态的政治运动的角度说,它是消沉避忌的;但从正常态的人性需求和发展的角度说,它何不是在积极寻求和回归生活呢!这应是“逍遥派”的本质所在。
之三,从政治上批判“逍遥派”的借端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从思想上指责“逍遥派”的说辞是“无政府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甚或在相关材料中还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至今仍然很时尚的词语),以至引出了“最新指示”,即“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多么骇人听闻啊!“逍遥派”所呈现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竟然关系到文革是否“胜利”!!
然而,恰恰是这个“关键问题”,赋予了“逍遥派”的形成和成型、形态和能量、扩展和传播,代表了一种社会集体心理的趋动和方向,那就是革命不能席卷生活,运动不能替代发展,批判不能消泯思想。
“逍遥派”并不成“派”,但它“离析革命”而去,且不断积聚起巨大的人流,它以个人爱好和情感,个人发展和成长为轴心的追求(此后遭遇批判的还有“养鱼热”、“养鸽热”、“换房热”、“奇装异服”、“三十六只脚”等),确确实实在潜移默化中,因情随事迁而构成了消解文革政治运动的社会基础。
附:邓小平谈“逍遥派”
查阅《邓小平文选》,在第二卷中有二处谈到“逍遥派”。
其一,邓在《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是选拔中青年干部》(1981年7月2日)一文中指出,很多材料反映,“文化大革命”以前几年大学毕业的,绝大多数是表现比较好的。这些人大体上年龄四十岁左右。这样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间表现不好的有,但大量是“逍遥派”。这是一个政治标准。
其二,邓在《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1982年7月4日)一文中,强调说,“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遥派”大多数还是比较好的。这些人应该好好地培养。一步一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快一点。
由此可见,文革开始不久就已经“靠边站”的邓小平,以他“旁观者清”的了解,认同“造反派”是少数,“逍遥派”是大量的。而这些“逍遥派”因没有参与革命造反,“大多数还是比较好的”,“这是一个政治标准”。正是这人数和表现方面的两个“大多数”,决定了邓小平认为“这些人应该好好地培养。一步一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快一点。”
这是邓小平的政治态度,具体则成为选拔和任用干部的标准之一。
作者:金大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相关链接;
文革初期复旦大学“斗鬼”风潮:不是“个案”是“常态”
|




